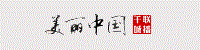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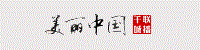
九乡一镇,草场面积占到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5%——达日的草原,成为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涵养地。
“这是两个月前,我在这里刚刚种下的草籽。”走进满掌乡查干村,罗日盖(上图,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供图)俯下身,小心翼翼地拿尺子测量起幼草高度,关切的神情就像呵护新生的婴儿。
戴着一顶藏式毡帽,并不高大但结实的身躯,粗粝黝黑的面容,罗日盖的样貌与高原腹地的牧民并无二致。只是那一副圆框细腿的眼镜和从不离身的笔记本,显露着他的身份——达日县自然资源局草原站站长。
在草原站,他已经干了快40年……
同事们眼里,罗日盖是无路不知、无地不晓的“活地图”。他出生在达日县一个普通藏族牧民家庭,因为学习过拖拉机驾驶和维修,“误打误撞”地被分配到了县草原站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,罗日盖每年在野外工作的时间都超过200天,“全县的土地几乎都是草场,咱不能蹲在办公室,必须把工作干在大地上。”
年复一年的坚持,他用脚步丈量了全县33个牧委会的角角落落。在外人看来并无区别的草原、山峰、河流,“不夸张地说,每一处我都能叫上名字,因为我都走过。”
在乡亲们眼里,罗日盖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“泥腿子”。这不,一见罗日盖,查干村的牧民先多就给他送上一个热情的拥抱。“今年春天,老站长带人到我家草场,又种下了20亩的草籽,还千叮咛万嘱咐,‘可别让牛羊吃了啊’。”说起罗日盖,先多竖起大拇指,“老站长真是个实干家,而且是咱基层牧民的救星。要不是他,恐怕我家的草地都得退化成黑土滩!”
先多说的黑土滩,是曾经令牧民闻之色变的“草原癌症”。
“众所周知,东北的黑土地是养分丰富的沃土,但只有一字之差的黑土滩,却是高原独有的生态退化现象。”罗日盖直言,自己工作40年,大半都在和黑土滩较劲,“由于过度放牧、气候变化等因素,草地植被退化后地表就会裸露出来,远看一片黑褐色,被称为黑土滩。如果不及时治理,再严重就会沙漠化!”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整个三江源地区都遭遇生态恶化。“人草畜矛盾激化,不少牧民不得不搬迁到异地他乡。”罗日盖记忆犹新,“就说这满掌乡,曾是全县草场退化最严重的一个乡,一度有七成草场退化为黑土滩。”
紧急时刻,国家启动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,在江河源头开始了一场保护“中华水塔”的绝地反击。退牧还草、人工种草、工程灭鼠、建设网围栏……罗日盖带着同事全年无休,先后修复黑土滩近80万亩,相当于7.5万个标准足球场大小。长年在草原上风餐露宿,罗日盖双膝关节严重受损,如今走起路来一瘸一拐。“不打紧,不打紧”,他笑着摆摆手,“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的草原,我这个草原站站长才算没白当!”
尽管年岁渐长,但罗日盖对新知识、新技术一直孜孜以求。行走在满掌乡,草地上不时能看到一些绿色的薄膜。“这是无纺布,在它的覆盖保护下,新种的草籽会长得更好。”罗日盖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起这一近几年应用起来的黑土滩治理技术,“草籽根部长得更深,抓地也更牢固,生态治理一定要讲科学!”
说着,他像孩子一样笑起来……